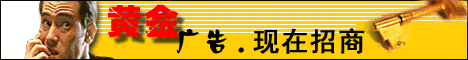编者按:
一纸工龄认定,非孤例——当“转工不转粮”的集体企业农民工撞上“未缴费不认工龄”的政策铁壁,折射的是历史转型期制度设计的深层断裂。
地方部门以“信访程序”消解行政责任,用“材料不全”回避实体审查,甚至以“一事不再理”关闭救济通道,暴露出程序空转对劳动者权利的侵蚀。而尘封的浙劳社老〔2002〕142号文(明确集体企业工龄视同规则)被长期搁置,更揭示选择性执法的治理惰性。
工龄认定本质是生命时间的政治估值。当三十三年前的劳作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,损害的不仅是个人养老金,更是制度公信力的根基。我们追问:如何弥合政策断层?怎样激活“抽屉里的法律”?答案关乎千万劳动者的尊严,更检验着社会治理的历史伦理。
——这不仅是高一平之战,更是对制度如何对待“时间债务”的终极诘问。

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
当“视同”成为“不认”的注脚
——一纸工龄认定背后的制度断层与权利困境
特约撰稿人 石磊 万民 夙来
在景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档案室里,一份编号为景人社法处〔2025〕03号的文件静静躺在铁皮柜中。这份决定书以不足两百字的篇幅,宣告了农民工高一平持续七年的工龄认定之路的终结:“与2018年诉求一致”“不再重复处理”。薄纸背后,是一个集体企业农民工跨越三十三年的身份困境——当“转工不转粮”的特殊身份遭遇“未缴费不认工龄”的政策铁壁,制度断层正在无声吞噬劳动者的历史足迹。
被遗忘的身份:集体合同工的制度夹缝
1992年的春天,当高一平以“转工不转粮”身份走进景宁县纺织器材厂时,他踏入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身份场域。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产物,“转工不转粮”农民工,被允许进入集体企业务工,却无法享受城镇户口附着的粮油配给与社保权利。这种制度性安排,本质是将劳动力商品化而拒绝承担社会再生产成本。
在浙劳险〔1995〕73号文件中,一个清晰可见,1996年前的浙江集体企业农民工参保尚属“自愿原则”。当高一平们手持集体劳动合同埋头劳作时,政策并未赋予他们参保资格——如同要求旱地里的秧苗自行汲水。然而,三十年后,人社局援引的浙人社发〔2015〕153号文件,却以“未缴费”为由否定了这段工龄,构成典型的历史语境错置。
更荒诞的是政策执行的逻辑悖论:当《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》第16条明确“因用人单位原因未参保可认定视同缴费”时,人社局却执着援引第18条“应当参保而未参保不认工龄”。这种选择性司法恰如为溺水者递上空杯——制度既未在当年给予他们盛水的容器,如今却指责他们未能盛满。
程序空转:行政机器中的权利湮灭
2018年,那个闷热的八月,当高一平收到景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《其他法定途径告知单》(LX20180046855926)时,他尚未意识到自己已坠入程序迷宫的入口。这份告知单将工龄认定申请标记为“信访事项”,悄然完成了一场法律性质的偷换。根据《信访条例》第14条,依法应通过行政程序处理的事项不得导入信访渠道,而工龄认定明确属于《社会保险法》授权的行政确认行为。
程序异化在此后七年不断升级:2025年4月,当高一平再次提交工龄认定申请,人社局重施故技出具《其他法定途径受理告知书》(景人社法受〔2025〕01号)。当申请人据理力争后,这台行政机器又发明出新的程序阻却——要求“通过现单位申请”。这种操作不仅违背《社会保险经办条例》第15条“社保部门应自行调取档案”的规定,更暴露了责任转嫁的意图:将集体企业的历史欠账,推给毫无关联的乡镇事业单位。
程序空转的终极形态出现在2025年6月24日的决定书中。人社局以“无新证据”为由终结程序时,刻意回避了两个关键事实:2025年提交的申请包含集体企业性质分析等新论证;而2018年处理的是信访事项,本次则是行政申请。这种刻意的概念混淆,恰如用昨日的餐券拒绝今日的饥民。
抽屉里的法律:被封印的权利凭证
在景宁县档案馆尘封的卷宗里,浙劳社老〔2002〕142号文第三条清晰载明:“集体所有制职工在1997年前连续工龄,经审核后视同缴费年限。”这份发布于二十三年前的文件,至今仍是解决高一平困境的直接依据。然而,在历年回复中,景宁县人社局始终对此视而不见,反而不断抬出针对国营企业的浙政〔1986〕52号文。
法律适用中的选择性失明,本质上是对制度正义的肢解。当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工龄认定问题的复函》(人社厅函〔2016〕3号文)强调“因国家政策调整导致未能参保的工龄应予认定”时,地方执行者却构筑起“材料不全—拒绝受理”的自动化响应机制。那些要求提供“劳动合原件”“养老保险缴费记录”的补正通知,对三十年前的集体企业农民工而言,无异于命令他们重现消逝的彩虹。
抽屉深处还锁着更具讽刺的凭证——2025年6月4日的《补正告知书》要求提供“单位函”。可景宁县纺织器材厂早在二十年前已改制消亡,就是现在的单位认可也是不现实。当制度要求死者为生者作证,其荒诞性已然解构了自身的正当性。
被折叠的人生:工龄认定背后的时空政治
工龄认定本质是一场关于时间权利的确认仪式。对高一平而言,1992.4-1995.8年不仅是四十一个月的劳作,更是青春资本的制度化兑换过程。当这段时光被排除在“视同缴费年限”之外,损害的不仅是养老金数额,更是劳动者生命时间的政治估值。
这种时间权利的剥夺具有代际传染性。在景宁县纺织器材厂同期工人名单中,刘奕标、吴耀伟、梅盛和等名字沉默排列。他们或许因生计所迫放弃申诉,但权利缺位形成的集体记忆,正在消解新生代对社保制度的信任基础。当年轻农民工目睹父辈工龄“蒸发”于政策断层,参保意愿必然遭受隐性侵蚀。
更深层的危机,是在于地方治理的时间伦理。景宁人社局七年间的程序循环——从信访推诿到材料苛求,再到“一事不再理”——实则是将历史问题抛向时间黑洞。当潘昌宝在2025年决定书上签下名字时,他终结的不仅是个案,更是地方政府对制度原罪的救赎可能。
在景宁的绵绵细雨中,若是原来人事部门及时收集个人档案的话,沙湾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的档案架上,高一平的人事档案里一定会仍夹着1992年的《集体劳动合同》。泛黄的纸页上,“转工不转粮”五个钢笔字洇染开来,恰似制度裂痕中渗出的泪水。
三十三年过去了,当年纺织器材厂机械的轰鸣早已沉寂,但历史债务的回响从未止息。当人社局的公章落在“不再重复处理”的结论上,它封存的不仅是一位农民工的工龄认定,更是一个时代对劳动者的制度承诺。
那些锁在抽屉里的法律条文,那些消失在改制浪潮中的集体企业,那些被“视同”二字消解的人生岁月的人,都在等待一个回答: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制度伦理,才能让劳动者在时光长河中不再溺亡于政策的断层?
制度的抽屉里,锁着多少被“视同”的人生?当法律成为文字游戏,程序沦为技术魔术,谁来为历史的债务签下认账的名字?